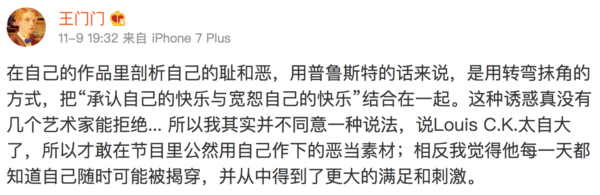看/听了三遍 Superbad, 太喜欢了所以写进段子。
– Call me by your name and I’ll call you by mine.
– McLovin.
– …Never mind.
去年有段时间发狂怀念青春期到呼吸困难,后来症状缓解。这段影评看哭我,糟乱甜蜜哀伤:
What makes the film so appealing is the disconnect between what comes from the mouths of these hormone-addled pups and what’s going on in their heads, where they’re still clinging desperately to the innocence they’re leaving behind.
最近重听 George Carlin. 老头儿通透,偏激,所以带劲。我在微博上贴了几条他专场里的原话,批判的是美国,但是放在国内那几天很应景。只能用这种方法表达愤怒,我更加愤怒。
他跟 Jon Stewart 的这段访谈是第一次听,这里是否也在讲自由意志的骗局:
You know, the luck stroke. Gotta have luck in this world. Part of it is your genetic makeup, that’s the luck. And then what you do is also partly genetic, because hard work is genetic. The desire to do hard work, the willingness to work hard and be determined and not be turned aside, that’s all genetic too. It can be altered to a little reinforcing.
有个模糊的印象,早前有朋友问我相不相信人有自由意志,我说当然啊,我的行为出于我的主观意愿。而提问的人持怀疑观点,是谁不记得了。我也早改变想法了。
这段记忆也可能是大脑的编排。就像前段时间我忽然觉得我原来有过笔友,但 TA 是男是女,哪里人,多大,怎么牵线的,毫无印象。感觉有多假,也就有多真。这个“笔友”在我的意识里影影绰绰,形迹可疑,如很多偶然冒出并侵扰我一时的记忆碎片。
都是生理过程。我还有长久的疑问:Is human brain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how itself works?
回到文字以前,回到赤身露体,回到阿法南方古猿,回到猴儿,回到鸟兽鳖虫,回到大海,回到单细胞,回到有机汤,回到混沌,回到零,回到由大脑结构决定其不可能理解的形态。
需要重看电影获得安慰,Billy Lynn, Mad Max, Gone Girl. 在 Billy Lynn 看到几点原来没太在意的 cliché, 稍微理解了某些批评。比如结尾处 Billy 和姐姐道别后,回到车上和闪回的 Shroom 对话,完全是为了明确角色动机而制造,给 Billy 的抉择一个直白的理由,为此不惜掩去人物的脆弱、惶惑。我对这种一定要把话说明白的、压倒性的转折感到失望,为什么不让观众承受一些不确定性?太驯化、太好莱坞。Mad Max 的沉默是金。
去亚特兰大连看三场电影,The Square, BPM, Jane, 都太棒了。如今要不是在影院,很难沉下心对着电脑看非中英文的片子。The Square, BPM, 加上去年的 Toni Erdmann, 欧洲电影的高度文明和高度野蛮,一股沉重生猛的力量,让人真正激动起来。都有极其鲜明的段落,反复想起反复惊叹——人猿在晚宴,性爱在病床,父女在迪厅,仅用文字概述就可体现戏剧张力。需要承受陌生感和不愉悦才可能真正欣赏。因此更讨厌口味保守、温情脉脉的“高分”电影——太被喜欢的,让我想拒绝。比如最近口碑极好的 Lady Bird, 烂番茄 100%, 每个人看完都是泪汪汪笑眯眯,包括我。零风险,毫无冒犯性,回想起来无趣到发狂。
纪录片 Human Flow, Dawson City: Frozen Time, Jane. 没想到在小地方的影院还能看到艾未未的片子,关于全球难民潮。专家学者政客出现不多,主要是一个地区接一个、一拨人接一拨地呈现,穿插艾未未自己的身影。还没上映就被保守人士攻击,说他为流民、罪犯辩护。我觉得这是艾伟大的一面,作为一个人(当然他有团队),走访同样是人的“他者”的苦难。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也算流民?再次想起《花脸巴儿》《老妈蹄花》。没有体会过生存层面风险的人,如果因为有人拍出这样的影像而愤怒,差不多是肉食者鄙了。Dawson City 里面那些一百年前的影像,淘金的人抓着绳索爬雪山,一条线上的蚂蚱,雪崩过来埋掉一截,两头的人再把他们扒出来。动物一样地活着。同样是旧日影像重新发现,Jane 记录了 Jane Goodall 在非洲走入黑猩猩社群的探索过程。片子一开始我就想,这个随行摄影师一定喜欢她,她也一定不讨厌摄影师,因为镜头中的她自然细致而美。果然,两人后来是情侣和夫妻。想起去年读的 Zoo Story 和当时对动物性 vs 人性的思考。
经典老片:在比赛日当天去看了 Dr. Stragelove, 厅里除了我只有一个人。几年前看的时候没充分体会里面的好,这次完全是爆笑。严肃活泼,库布里克伟大!去年在影院看《发条橙》,我对自己的反应很意外,没有了头两三次看的震惊和不适,取而代之是欣赏讽刺的愉悦,沉浸在一种 bouncy 的节奏感中,简直要怀疑我是不是变得 too sick to feel sick. 感恩节当晚看了黑色讽刺戏,也是一直想看的 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成功中和掉一些温馨祥和的气氛。最早知道的是中文译名《灵欲春宵》,看过之后才知道故事本身和字面一样耸动。房东他爹提供了录像带,这是我头一回用录像带看电影。婚姻关系中的操纵游戏,玩到最后谁也离不开谁,因为只有他们俩明白游戏规则和退出的代价(所以我重温了 Gone Girl)。经历过五次婚姻、年逾八十的房东她爹说:这是我这辈子看过的最黑暗的电影。
电影以外的其他,更使我发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