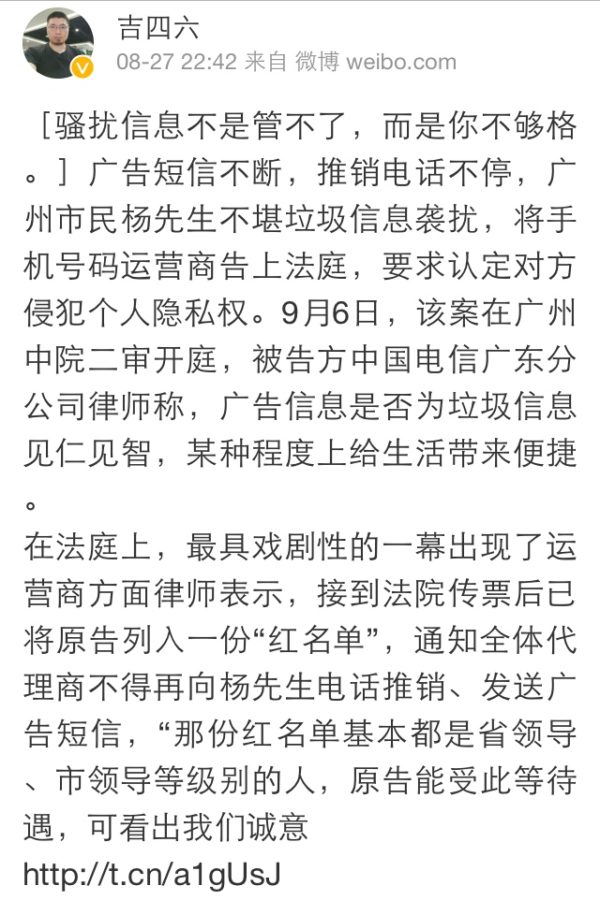班里组织中秋晚会。
老师统计谁要玩游戏,我报了名,隐隐有种能跟喜欢的人一起 party 的期待。
我快速看了眼名单,没有比尔。
大家听完老师讲话,躁动起来准备 high. 有同学问我要不要一起玩,我说要先去洗手间。
不知怎么端了一杯酒在手里,绿色,大概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满。我去加冰,流出来一些水和少量冰块。现在杯子一半满了,从上到下呈现出透明到翠绿的过渡。朋友的酒是另一种颜色,装在锥形瓶一样的玻璃小瓶里。
我在洗手间磨蹭半天,在镜子前站着,不是在化妆。洗手间是很旧的陈设重新粉刷的。
出去之后门口有两三个同学在等我。我们往教室走,刚一进前门,看到一个 MC 在讲台上问大家问题,台下密密麻麻的人。MC 一吼,台下齐刷刷作答。
我说,问题不是老师刚问过了吗?
可能怕刚才有人没在,朋友说。
教室没开灯,只有一束追光扫来扫去,忽然扫到我这里。我感到我的脸强力反射了一部分光线。
在这一瞬间,我看到人群中的比尔看到了我。他随即背过身去,剩一个白色上衣的背影。但是在强光的炫目之下比尔可能只是我一个幻觉。
我被环境中不均匀分布的压力的综合作用推着走,回到自己的座位。课桌不是一张一张分开的,而是左中右三组。我的大概在中间偏左后。
一个男生笑咪咪的看着我回位,非常谦和有礼。他和我一排,是个老好人。我记得我和他中间隔一个人。
我回头问朋友,你要进去坐吗?她示意我去。我挨着笑咪咪的男生坐下,感觉不太好,大家都坐得太规矩了,完全没有开趴的气氛。
朋友去教室左后角和另一个朴素女生讨论问题,又忽然跑过来问我,你有没有白糖?我们做那道题需要白糖。
我很生气,手伸进书包胡乱一摸:没有。你要不就找别人借,反正我是没有。你非得现在做题吗?
她很着急,又茫然,似乎没觉得向别人借是个办法。她的着急让人烦躁。
我再次告诉她我没有,你看着办吧。
她颓然回到座位,在我旁边摊开习题,说只熬到十二点多就结束。
我抬头环视,大家都在讨论题目或做卷子,连比尔也是。但这可能是我的推测,我不一定有勇气直接在人群里搜索他。
我很生气,就是不愿意学习,感觉被一群人骗了,老师和同学。我是断然不会留下了,快速收拾好书包,推开朋友走了。
在夜里往校外荒凉的停车场走。过马路的时候,驶来一辆没装车窗的吉普,司机带墨镜,头发半长,高晓松的脸型。他往学校拐弯,车速慢慢降下,头略伸出,盯住我的方向,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改变主意向我过来。
我忽然想起独行女生半夜被劫掠的种种,吓得跑到路的另一侧,向开过来的另一辆 SUV 招手。SUV 大灯刺目,司机也并没减速,但吉普男看我铁了心要求救的样子,扭头开走了。
我还是害怕,往停车场走在沙石路上也没有安全感。停车场里一些男人走动,也不是刚停了车,也不是要开车离开。有的似乎住在停车场周围的窝棚,这里就是他们的生活区。
我在沙石、杂草、几乎不见的停车线和场地外缘走了两趟,没有我的车。我又到连通着的另一个小停车场看,没有。最后一个,略远一点的,我走上坡去查看,也没有。
我开始心慌,努力回想自己把车停在哪里,毫无印象。迎面遇到一个学校管理方面的女人,看起来盛气凌人,我问她怎么回事。
她说,停车场的人不满学校对车辆的管理,觉得没有自治权,拿我的车说事,拖走了,如果想要回来得到某某地点提车。
我语气不好地问她:你是说我的车被拖走了?
她:嗯。
我气得扭头跑了,不忘回身愤愤说声谢谢。
回到第一个停车场,我对一个坐在窝棚前面、管理人员模样的背心老头说,我刚刚找了几遍,发现车不见了。
他心不在焉地说,猫找到了,找到了。没有看我,手上一边胡撸了两遍肥猫。
我说,不是猫,是我的车,学校的人说是被拖走了。
老头说,哦!是的。拖走了。他们检查你车的时候把车门重重摔了两次,我看不下去。之前也是,老是粗暴对待你们的车。
我说,没错,设立各种标准把想人拒之停车场外,还经常随意弄开车门检查,把你车里的东西搞坏。
老头说,所以我们叫人把你的车运走,给他们个下马威。
说话间,我环视停车场,远处的杂草灌木丛窸窸窣窣,一只马一样大的鸵鸟一探一探地走过去。
我站在停车场里,想要找自己认识的车或人载我回家。忽然想到这样成功几率太小,于是走到路边,这样去往三个停车场的人我都能瞧见。
午夜的星光下稀稀拉拉有人从学校出来,我仍然带着热望,觉得比尔一定能在其他人出来之前接上我。
这其中隐含的一厢情愿包括:比尔一定还没走,比尔一定有车,比尔的车一定停在这里。以及……
我在这情愿中抵达了无意识的深处。
(为了不方便区分,我打算把所有梦里的男主角都叫做比尔。)